【政策分析】记忆外交:如何利用过去制定未来外交决策?| 国政学人 第333期

作品简介
【作者】Kathrin Bachleitner,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宜家基金会研究员与国际发展学院(难民研究中心)成员,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准成员。研究重点为国际关系中的集体身份、记忆与价值观。
【编译】张曼娜(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校对】贺凡熙
【审核】刘潇昱
【来源】Kathrin Bachleitner, Diplomacy with Memory: How the Past Is Employed for Futur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ume 15, Issue 4, October 2019, Pages 492–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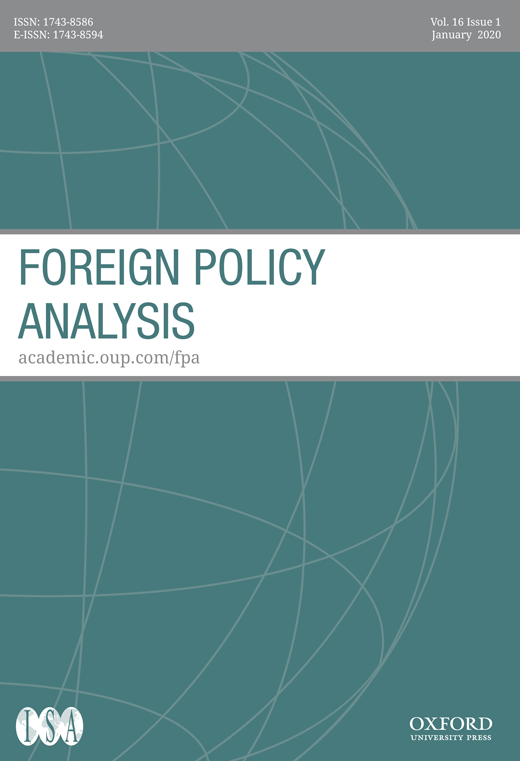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外交政策分析》杂志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代表国际研究协会出版的季刊。该期刊旨在以比较或具体案例研究的方式研究外交政策决策的过程、效果、原因或结果。反映了该领域的多样性、比较性和多学科性质,为研究出版物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论坛,加强了跨越理论、方法、地理和学科边界的概念和思想交流。期刊影响因子为1.012。
记忆外交:如何利用过去制定未来的外交决策
Diplomacy with Memory: How the Past Is Employed for Future Foreign Policy

本文认为,有着共同创伤过去的国家间存在着国际政治行为的另一种形式,即记忆外交。记忆外交是指官方的外交团队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实现理性目标而传递某种历史形象的行为。首先,文章搭建了一个理论与实证的框架,强调记忆外交作为一种战略外交行为,不符合有关国家行为的主流国际关系模型。第二部分,作者将该模型放在两个选定的冲突后场景中进行检验:西德和以色列、奥地利与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向犹太国家支付最终赔款的双边谈判。从这些历史案例中提取记忆外交的核心要素后,本文认为应当利用记忆对传统外交战略工具进行修改,以便更好地解释其他冲突后情况下的国家行为。
文章导读
一、 集体记忆与国际关系
二.“记忆外交”模型
三、记忆外交的应用:1952年对以色列赔款案
(一) 打造负罪外交:西德与以色列赔款问题
(二) 打造无辜外交:奥地利与以色列赔款问题
(三) 对“记忆外交”模型的启示:奥地利与西德的案例对比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