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研究】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理论 | 国政学人 第32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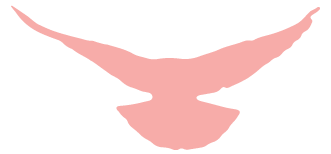

作品简介
【编译】许文婷(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
【校对】崔涵宇
【排版】赵怡雯
【来源】
Pitts, Jennifer. “Political Theory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no. 1, 2010, pp. 211-235,doi:10.1146/annurev.polisci.051508.214538.
期刊简介

根据2018年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其2018年的影响因子为3.915。

文章导读
过去十年中,有关帝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的作品大量涌现。其中许多作品集中于探讨帝国在许多经典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在现代自由主义和相关领域,例如后殖民时代的移民社会和国际法学科的形成中的作用。与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等领域相比,政治理论在帝国研究方面是后来者,这些学科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研究现代欧洲帝国的历史和遗产。但除去布什政府时期对“美国帝国主义”问题的集中关注外,政治理论一直未能有效地分析当今全球秩序中的帝国主义因素,例如强权国家对世界范围内极端贫穷、生态危机、国内冲突和暴政状况所负有的重大责任。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近年来的政治思想史文献关注的焦点,即帝国在经典政治思想家作品中的地位。一直到最近十年,他们思想中“帝国”这一维度相对而言都被忽视了。第二部分的讨论重点是自由主义与帝国在理论和历史层面的关联。这一问题本身又隶属于一系列更广泛的有关普遍主义如何处理帝国遗留下来的道德、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的问题。本文不时回顾有关自由主义和帝国的问题,它们在有关移民社会(第三部分)、当代新自由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第四部分)、全球正义(第五部分)和国际法(第六部分)的文献中屡见不鲜。作为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对话的回应,新的一派学者开始对帝国权力进行理论化(第七部分)。最终(第八部分),政治理论家们姗姗来迟地开始探索后殖民研究的创新和关注如何重塑了他们的研究主题,虽然后殖民研究本身也经历了长时间的自我审视。
人类学家仍然是对帝国主义和后殖民政治及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互动最犀利的分析者之一。文学和历史学科也很快(即使是没有完全地)被后殖民研究所改变,这通常以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为标志。最近的一个中心主题是欧洲的国家结构和国族认同是如何通过帝国的建设而部分地被建构起来的。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最近也开始涉及帝国的话题,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他们这个经常被边缘化的地区出现的新理论中心。美国既是一个在整个19世纪征服并吸收了广大大陆领土的移民社会,又是20世纪古巴和菲律宾等非合并领土的统治者,这一地区的帝国历史正越来越被广泛地研究,并被认为是当代许多事件的背景。但尽管人们对非欧洲的帝国,例如古代中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重新投以关注,政治理论讨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的帝国。
本文并不对“帝国的”和“殖民的”做系统性的区分。帝国领土和殖民领土之间的一个通用的区分方式是,殖民领土指涉及大量从宗主国中心城市而来的定居者的领土,而“帝国”一词则强调对其他领土的广泛统治。但是,官方的、流行的、甚至是学术上的用法都是不固定的,并且“殖民地”和“后殖民地”这两个术语同样适用于具有明显定居点或没有定居点的空间。实际上,前者现在往往被描述为“定居者殖民地”。因此,“殖民帝国”通常指“帝国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剥削性经济关系”或“对全球中心以外地区的占领和吞并,以及对外国主权的夺取”。而“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正如政治上的许多“主义”那样,既强调权力实施的程度,也强调其不可靠性。
一、政治思想史
政治思想史的最新文献表明,帝国主义对政治理论经典中许多关键人物的理论和专业关注焦点以及对更广泛的近代政治语言和意识形态都有重要影响。自欧洲与新世界的相遇以来,近代政治思想就引起了人们最多的关注,这并不令人吃惊,但帝国也被证明是研究早期思想家的有启发性的视角。以帝国为主题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是由几位采取广义的剑桥学派方法的学者开创的,包括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约翰·波考克(J.G.A Pocock)、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和最近的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帕戈登早期的开创性成果探索了有关西班牙在新世界统治合法性的辩论。在说明帝国如何产生新的国家和政治形式,以及塑造例如民主共和等近代政治意识形态时,帕格登为帝国在政治理论中的中心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案例。塔利把与帝国有关的问题置于洛克思想和近代立宪主义的核心中。刚好相反的是,波考克则坚持必须以帝国和全球的眼光来理解英国的历史和政治思想。他探索了当时“帝国”的广泛含义和他所说的那个时代的“海上帝国危机”(crisis of seaborne empires),以及当时许多政治和社会思想家对本应在征服时代获得成功的全球贸易的失序的焦虑。而正如塔克所言,有关主观权利的早期近代理论家是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构想主权个人,反之亦然。他们制定了自己的理论,对土著人民和非欧洲人民产生了“通常很残酷的影响”,这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欧洲商业和帝国扩张引起的两个关键的实际问题:对亚洲的贸易和航海自由与控制的争夺,以及各国将其在新世界的定居殖民地合法化的努力。
正如近来学者们强调的那样,许多关键的政治理论家以立法者、外贸公司的雇员或合伙人的身份积极参与了欧洲在本土之外的贸易与征服,这提升了这些行动对欧洲政治思想史发展的重要性。例如近来的文献研究了格劳秀斯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持续进行的理论和法律工作。洛克的财产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的殖民统治相联系,更具体地说,与他在起草《卡罗来纳州宪法》中的工作有关,但最近的学术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他在州宪法起草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这种参与程度对他关于财产、主权和自由思想的影响的理解。
如今众所周知的是,要全面理解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以及他们为之做出贡献的传统,就需要其帝国和全球背景与关注。学术研究清楚地表明,欧洲政治思想的关键概念和语言,例如自由与专制、自治和自主个体观点等都是随着帝国主义和商业扩展到欧洲之外而产生的。正如我们必须理解现代西方宪政民主(和国际法)是在帝国背景下出现的一样,我们也必须在政治思想的传统中理解其支持者,并且在同样的全球和帝国背景下理解其他被继承的政治形式与概念的支持者。这通常会把思想家们带回一个他们本人也觉得很重要、但被后世读者忽视的语境中,这对18世纪的思想家们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史密斯(Smith)、康德(Kant)等。其他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密尔(Mill)和托克维尔(Tocqueville)也许对他们的帝国背景对其理论的重要性轻描淡写,但只有我们掌握了他们的职业和思想中的帝国维度后,他们的知识和利益的延展范围和局限性,以及那些显然普世的道德和政治主张的局限性才变得明晰。
二、自由主义与帝国
三、移民社会中的后殖民困境
五、全球化、世界主义和全球正义
六、国际法
七、对作为政治体系的帝国进行理论化
八、“后殖民研究”之后
一些观察家已经准备好考虑在布什政府统治结束后美帝国主义的危险,这些事态发展产生了丰富的跨学科交流,它们应当有助于加深和活跃政治理论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