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编译】王栋:为什么没有东北亚安全架构?—评估影响东亚稳定的战略障碍 | 国政学人 第31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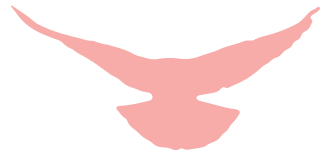

作品简介
【作者】王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历史与政治学系终身制(tenure-track) 助理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教育部基地)执行主任,兼任欧美同学会东亚安全论坛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环球时报-卡特中心”中美青年学者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等。他是《国际展望》和Northeast Asia History等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编辑委员会委员,也是Foreign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International Affairs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冷战史、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等,是第一位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的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会刊Diplomatic History 单独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曾入选慕尼黑青年领袖、北京首届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人文社科排名第一)。
Friso M. S. Stevens,莱顿大学安全与全球事务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政治学讲师。
【编译】施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审校】施榕、陈勇
【排版】李佳霖
【来源】Dong Wang & Friso M. S. Stevens (2020):Why is there no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 Assessing the strategic impediments to a stable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DOI: 10.1080/09512748.2019.1702087
期刊简介

The Pacific Review,《太平洋评论》是太平洋地区研究的主要平台,作为跨学科期刊,其宗旨和目标为打破研究领域之间以及学术界、新闻界、政府和商界之间的壁垒,重点关注政策问题。2018年该刊的影响因子为1.865,在区域研究类SSCI期刊中排名9/47,在国际关系类SSCI期刊中排名第22/91。

王栋

文章导读
本文探讨了存在于东北亚地区的“组织鸿沟”(organization gap),试图解释为什么该地区没有最低程度的、多伊奇式的安全共同体。作者辨别了四个阻碍因素:强调岛屿争端是国家之间彼此深刻怨恨的表现,而这种怨恨是由历史上的战争和敌对所形塑的; 一种与集体记忆有关并用以突出“他者”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中美战略互疑与竞争;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范式的宿命论逻辑不同,本文深入探讨了使东北亚地区内相互对立的阵营得以维系的深层且相互关联的障碍。要实现怀特和基辛格所提出的“协调”或“共同体”意味着首先应该考察东北亚地区独特的结构、权力以及国内社会-历史的动态。在此过程中,本文提出了在何种条件下“去安全化”这一过程能导致东北亚地区内出现共同体。
一、理论上的争论
20世纪50年代,多伊奇发展和完善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而阿德勒和巴奈特则在冷战体系缺乏灵活性之后重拾这一概念,认为冷战体系内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竞争压力、互疑以及对抗可以被改变。21世纪10年代初,学者们再次开始讨论建立一个东北亚安全架构的可行性(Lee & Pempel, 2012;Seliger & Pascha, 2011)。在一个被奥利·维夫称之为“去安全化”的过程中,相互的安全关切得到改善,并逐渐被对和平合作与信任的共同认同所取代。然而,就像围绕安全共同体的争论在美苏对抗的几十年里处于休眠状态一样,弗里德伯格所称的“悲观主义现实派”主导了关于亚太地区内的中美关系应如何被管理的争论。例如,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分别提出,美国应该制衡或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加强美国领导的轴辐体系。在他们看来,东亚地区内激烈的安全竞争或中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稍微不那么悲观的学者,如艾利森认为,在极度审慎的条件下,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十分勉强。与此同时,赵汀阳和康灿雄甚至主张回归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或天下体系,将其作为为中国及其直接邻国创造和平地区环境的最佳方式。还有一些学者,如阎学通和漆海霞呼吁中国寻求自己的同盟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朝. 鲜和俄罗斯,以平衡美国在本地区的压倒性力量和同盟体系。
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东亚地区的中美安全困境正在加剧,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也卷入其中,但国际政治中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不一定是故事的结局(Booth & Wheeler, 2008,pp.295-296页; Lee, 2017)。事实上,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应该超越彭佩尔(Pempel)所指出的在西方学界对东亚,特别是东北亚安全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一种关于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的单边主义和现状偏见。怀特和基辛格阐明了如何将一个复兴的中国和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的美国容纳进一个新的、共同的地区秩序,并提出建立一个亚太大国的“协调”或“共同体”。怀特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欧洲协调”的权力平衡方式,而基辛格则主张建立一种“共同的事业”,在这一“共同的事业”中,中国和美国都必须把对方视为“地区安全伙伴”,并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一套共同的习惯与实践。
然而,与安全维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2000年代末,东北亚地区一直站在金融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沿。更重要的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学术领域。以东盟的成功为基础,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主张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呼应了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Koizumi)和鸠山由纪夫(Hatoyama)的尝试。同时采用结构分析和社会-历史及观念的分析,我们专注于区域的努力可以最好被描述为受到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启发。实际上正如布赞所指出的, 东亚地区权力均衡发生变化是该区域体系内中国的相对崛起、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日益紧密的安全联系、显著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和相互依赖的共同结果,这一变化的权力均衡塑造了东亚地区如今的面貌。
二、效仿东盟
考虑到东北亚地区的首要需求是建立基本水平的战略互信,以及东北亚仍深陷于赫兹所说的“你死我活(kill or perish)”的安全困境中的事实,对东北亚地区而言最适合作为效仿标杆的一体化程度是东盟模式的最低制度化水平。那些后来被称为“东盟方式”的社会化进程以规范为基础,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伊奇式的共同体的特征: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不受外来势力干涉的区域自治和安全上的自给自足,例如:没有排他性的多边军事协定,以及最关键的:不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政。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存在“一种真正的保证,即成员国不会互相斗争,而是会以某些其他方式解决它们的争端”(Deutsch, et al., 1957, p. 5)。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新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认为自己国力弱小且国内四分五裂,各国在历史经验和社会文化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寻求在不团结中得以团结起来的方法。面对来自冷战大国的外部压力(Storey, 2011,p.25),东盟的创始成员国决定建立一个共同体来缓解它们的共同弱点。这一共同体是在各成员国社会中已有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共有的思想和关切是:民族主义、国族建设、社会分裂和外部干预的历史记录和民族自决(Ba, 2009,chap. 1)。更重要的是,东盟的制度结构和建立共识的机制反映了这些脆弱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创始者们的目标是利用东盟的规范和理念,建立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安全共同体。在运作这些规范和观念的同时,东南亚文化特有的“东盟方式”在社会化过程中被采用;讨论是非正式的、不连续的、包容的、协商一致的、非对抗性的和不具有约束力的(Acharya, 2009, p.55; see also Bellamy, 2004)。这些非正式对话的目的是在具有显著差异的成员之间维持微妙的统一,而不一定是产生牢固的协议或宣言。仅仅是举行会议和对话、讨论紧迫问题这一事实,就为各国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因而缓解了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对外呈现出一个统一的集体形象。重要的是,在后殖民时代这些国家的精英们最终找到了一种建设性的方式,使根植于各自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得以推动而非阻碍一体化进程。考虑到东北亚各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类似分歧,这种构建共同体的多元的或“交易主义”的方式——即保持各自主权的完整——特别适合东北亚地区。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地区就面临着许多如今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为了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东北亚安全架构的缺失——维夫提出的去安全化的第一阶段,即如何从不安全状态过渡到安全状态应该是我们研究的目标。本文的其余部分利用前文所述的多伊奇式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理论概念,试图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以及哪些结构性的和观念上的因素导致许多人所提出的东北亚共同区域秩序没有实现。在辨别对地区信任与合作构成最大阻碍的问题时,我们重点关注以朝. 鲜半岛为战略重心的中美日三国关系。尽管在过去5年中,半岛紧张局势逐步升级,但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却早已存在。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并且在当前东北亚关系中根深蒂固。人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本文所提出的四个障碍是在既有文献中被反复讨论和争论的,但这些讨论却是分开的。因此,我们在评估这四个障碍之后主张采用一个整体性的方法来解决妨碍安全合作的根本因素。
三、中韩关系与美国的防卫态势
乍一看,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好,因此两国围绕中国东海内苏岩礁产生的争端有任何升级的态势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尽管双边关系相当稳定,但两国自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几十年里,两国之间是极度不信任的,其根源在于两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记忆以及此后的中朝同盟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影响当今两国关系的因素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改革计划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才在“睦邻政策”的支持下与韩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Chung, 2007, pp.69-70)。然而,随后的友好关系和互利的经济相互依赖并没有使围绕苏岩礁所产生的持久争端有任何缓和。事实上,和平解决争端的遥遥无期一直是阻碍邻国间信任与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两国在黄海的专属经济区存在重叠以及它们在解决方案上的分歧。韩国声称该暗礁更接近其最南端的马罗岛,专属经济区应该以中间线来划定 (Jung, 2008)。中方认为,由于岛礁的水下地形,它不能产生任何领土权利;双边谈判是唯一的出路 (Zhao, 2012)。中韩在专属经济区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也对韩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产生了影响,这当然与多边军事协定有关。尽管美国对这一争端本身没有采取直接立场,但美国有保护韩国的条约义务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影响以及苏岩礁争端升级的可能。
此外,一度暂停的美韩联合军演“乙支自由卫士”(Ulchi Freedom Guardian)也经常在黄海举行。考虑到黄海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对这一军演的敏感及其所提出的关切。作为通往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地带的战略门户,它们一直是外国侵略者首选的侵略路线,这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而且到了1895年,日本确实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夺取了朝鲜并吞并了台湾。因此,中国认为韩国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与日本一样,韩国能够而且一直是美国宣示实力的舞台——例如,冷战期间台湾海峡的三次危机。作为美国轴辐体系的主要锚点,韩国和日本获得了美国对它们防务的坚定承诺。可以肯定的是,韩国和日本在岛屿争端问题上的自信立场——与它们的相对物质实力不完全相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其美国同盟承诺背后强大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来解释。
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在地区内扮演主导性的角色,这将我们引向了韩国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如何平衡中国对美国势力存在于韩国的担忧,以及过度依赖中国经济需求所带来的波动性与保持美国军事介入韩国以应对朝鲜威胁的需要?这一难题的严重性在2016年7月韩国决定部署先进的“萨德”(THAAD)导弹防御系统所引发的敌意中得到了体现。中国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回应,利用地缘经济杠杆和庞大的消费基础来对特定的韩国产业如旅游业、汽车制造业和食品零售业(Paik, 2019)加以惩罚。虽然韩国方面辩称,此举只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然而,先进的X波段雷达系统将美国的触角延伸到中国大陆,可能危及到中国自身的战略防御能力,这是中国对部署萨德做出如此强烈反应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些担忧还包括日本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在对朝鲜导弹试验的忧虑加剧之后,安倍晋三内阁增加了第三层导弹防御系统。在中国看来,这些系统与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部署的兵力和美国第七舰队相结合,损害了中国投射可靠的常规及核威慑力量的能力,也进而有损其保护本土不受攻击的能力(Goldstein, 2000, pp.28-29)。让中国方面尤其无法接受的是这可能有损中国确保对美国进行二次核打击报复的战略威慑能力(Zhao, 2016, pp. 4-5)。因此,在结构层面上,域外大国的存在及其在东亚地区的排他性军事同盟体系不仅限制了韩国在对华关系上的政策选择,也阻碍了任何根本性的、多层次的区域一体化。只要韩国和日本是一个排他性阵营的成员,任何安全保证或解决争端的举措都是空中楼阁,更不用说构建一个与东盟类似的、能带来安全相互依赖的最低程度的共同体了。
四、韩日之间的敌意和三方同盟的缺失
然而,真正对安全领域的合作构成障碍的实际上并不是韩国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对过去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记忆,以及韩国的当代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反日情绪。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以及诸如朝鲜之类的共同挑战,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认为它们有更深层的安全关系。此外,两者都被定义为所谓的成熟的民主国家。虽然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们也承认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有一定的道理,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的制度倾向于维护另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这是形成同盟的前提(Doyle, 1983; Owen,1994)。
总而言之,与这些非常有利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韩国对日本根深蒂固的憎恨。这可以从历史当中寻求解释,即韩国和日本围绕独岛/竹岛岛群展开的争端。可以肯定的是韩国倾向于选择维持现状,保持对该岛群事实上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导致韩美日的三角关系出现战略模糊从而削弱了对朝鲜的威慑。韩国的这一选择偏好不能从严格的理性角度来解释。虽然在上一部分论述的主要障碍涉及结构方面,但这里显然是意图和动机的不透明在阻碍安全领域的和解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超过一半的韩国公众对日本有不好的印象,其中超过80%的人认为日本未能“反思其入侵韩国的历史”,四分之三的人提到了独岛争端。然而,尽管韩国从独特的历史视角来看待日本,但正如我们将在中国的处境中所看到的那样,准确判断历史事件及其影响与探讨这些长期蛰伏的问题为何以及如何浮出水面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追溯两国关系恶化的过程中——直到2005年两国关系仍处在合理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看到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以及韩国国内的驱动因素。在日本的修正主义行为方面,2005年有三件大事:岛根县发布了一份“公告”,将一个世纪前日本正式吞并韩国的那一天定为“竹岛日”;采用“右翼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书;以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
虽然这些事件无疑进一步恶化了双方对彼此的看法,但是更准确地来说应该从公民社会团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自199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所采取的强硬立场来看待这些事件,民族主义运动和韩国政府的强硬立场使其很难与日本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Wiegand, 2015,p. 356 ff)。事实上,正是西式民主政府固有的运作方式使其受到韩国公众舆论的约束,进而限制了韩国政治领导层的斡旋空间(Fearon, 1994)。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民主化”开辟了新的信息和表达渠道,为这些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组织和影响公共话语铺平了道路(Kingston, 2017 , p. 111)。他们所拥护的是一种基于共同祖先的、与朝鲜半岛有着强烈历史联系的和有着激烈反日情绪的民族主义形式。日本的修正主义行为和韩国政府在社会中灌输反日民族主义叙事的政策表明,我们所考察的第二对关系在观念领域受到了最明显的阻碍。日本和韩国已经重申了过去的敌对身份,创造了一种“自我强化的竞争”,使它们之间的合作难以从经济依赖跨越到安全领域并塑造团结和信任的相互形象(Buzan et al.,1998,pp. 36-37)。当它们在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不断恶化和被调动起来时,很难想象双方能够按照独特的“东北亚方式”努力塑造共同的身份。因此,任何观念上的转变和成功的政府间交流都要求两国政府首先从下而上地改变它们的认同政策,对日本而言尤其需要从改变公共外交领域的政策开始。
五、钓鱼岛争端和民族主义的角色
同样在中日关系中,岛屿争端常常成为焦点,是深刻的未解的历史敌意的一种表现。中日的岛屿争端主要围绕东海上的八个无人定居岛屿即钓鱼岛展开。中国强调自身的主权诉求是基于历史上的中国和外国的地图以及和琉球王国的朝贡关系。据此,中国主张自身对钓鱼岛的联系和控制可追溯至14世纪,当时的渔民就已利用这些岛屿作为导航信标。而作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的一部分,中国被迫将这些岛屿割让给了日本。因此,中方认为,在日本帝国崩溃之后,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的要求,钓鱼岛应归还中国(中国外交部, 2012年)。
在钓鱼岛争端中,日本采用了与其在独岛/竹岛主权争议中相似的解释逻辑:日本声称其在钓鱼岛为无主地时就已“发现”它们,并在1895年通过内阁决议将其纳入日本领土,与“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和中国被击败等事件无关(Japanese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6b)。日本政府同时宣称,在1972年美国放弃对冲绳的控制并将联合国授权的对岛屿的管治权移交给日本之后,钓鱼岛就一直处于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McCormack,2011)。
正如前文在讨论日韩两国的紧张关系时所指出的,造成这种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是日本明治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以及日本不愿承认与其崛起过程相伴的侵略和战争罪行。中国与韩国的战争记忆可上溯至1895中日甲午战争年,中国当时输给了被认为是在文化上劣于自己的国家,韩国则失去了朝贡关系的安全庇护,导致它的人力和资源在此后的五十年内更容易受到日本的掠夺。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完全解释为何受害者的记忆和身份仍然在当代的公共话语和中国对日关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中日公众层面的相互认知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非常正面,但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开始,这种历经多年辛勤培育的民间联系被政治上的矛盾所破坏,宣告“历史问题的时代”的开启(Westad, 2013,pp. 414–415)。在各自重建身份认同之后,中日两国对国家利益的解读和其中各项内容的等级划分发生了变化,同样改变的还有各自对对方国家能力的理解 (Wendt,1992, pp. 397–398)。当东盟各国的精英利用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建设性地将“一个东南亚”的观念引入本国时,东北亚却未能将社会认同建立在儒家传统和共同利益之上,相互的敌意和怀疑反而削弱了认同感。
作为东亚整体趋势的一部分,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加强正当性、强化社会凝聚力和身份认同、动员社会紧密团结在共同目标周围的有效工具。那些有着被殖民或被侵略历史的国家尤其渴望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然而,关于“(民族)独特性”的观点在东亚国家的政府中得到了支持,特别是当其与另一个民族的类似观念相冲突时,这种叙事常常能自己不断发展。韩国和日本采取了相似的民族主义程式,各自将针对另一方的“敌对叙事”纳入本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式体现为对“百年耻辱”中遭受日本侵略的历史叙事。
相应地,中国和韩国对日本企图否认其战争侵略历史的批评也引发了日本在经济相对衰退后已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弹(Suzuki,2015)。作为日本战后外交的战略处方和社会的观念支柱,“吉田路线”(Yoshida Consensus)以经济发展、和平主义和对美日同盟的依赖为中心,但经济奇迹的终结使其走向瓦解。在此背景下,安倍晋三上台执政,施行以国家振兴为目标的政纲。安倍政府将推动经济复苏和出台更强力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相捆绑,实施了促进日本“正常化”的“爱国主义”改革(Berger,2014)。然而,由于东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认为日本并未完全对其过往罪行表示悔过,日本的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东亚地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恐惧。
六、美国轴心/再平衡与中美安全困境
这部分主要关注中美关系,聚焦于美国的防卫态势及其与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东亚地区的美国同盟体系与中美敌对局面和安全困境被认为是走向“去安全化”过程中的最根深蒂固和难以克服的障碍,更不必说构建“太平洋共同体” (Pacific Community)(Cha, 2009; Christensen,1999; Liff, 2018)。在东北亚地区,对立阵营之间螺旋式上升的疑虑和军备竞赛使得敌人意象和对抗行为长期存在,其背后的主导性观念是:如果其中一方在军备竞赛中落后,或者另一方在合作博弈中出现了背叛的行为,则国家本身或者其政治体系的独立和生存都将岌岌可危(Jervis, 1978, pp. 167–168ff)。缓解这一困境需要理解中美对抗行为逐渐强化的动因。
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的战略疑虑源于朝. 鲜战争后美国与盟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奥巴马政府改进冷战时期出现的轴辐体系的举动更是加剧了这种疑虑。从中国的视角看,奥巴马提出的“转向/再平衡”叙事似乎完美契合了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政策处方,即制衡和遏制中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重大转变,在亚太方面的政策路径被重新命名为“印太战略”。但从实际意义层面和战略层面考虑,它事实上仍然是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的延续。由于支持再平衡战略的美国区域基地体系和使之得以推行的对盟友的安全保障几乎都仍然存在,可以认为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是不带有“再平衡”标签的再平衡战略。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提出新的战略名称来)至少在政治层面与前任政府保持名义上的距离,但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首次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举动还是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仍在履行奥巴马时期做出的将战略资产向亚太地区重新配置的承诺。
回顾本节内容,可以清晰地发现有两大因素阻碍了中美超越“你死我活(kill or perish)”现状的努力。首先是对彼此军力部署的恐惧。中美攻守平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体现在特定海军装备内在的功能模糊性上(Kaplan, 2010, p. 34),用于防御的武器可能也会被用于进攻(Jervis, 1976, p. 64)。判断一艘海军舰艇究竟是用于海底考察还是服务于进攻目的存在困难,致使中美安全困境更加严重(Jervis, 1978, pp.186–188)。其次,国家同样不确定未来的军事力量体系是否足以遏制进攻和保障国家生存。更重要的是,在由各国国家力量构成的体系结构中,国家的相对位置对东亚区域的权力平衡有着怎样的意义?最后,这种体系背后的国家实力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为回应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美国正投入“必要”的资源提升海军实力来弥补传统的权力投射方式(的不足),以维持在东亚地区的霸权(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总而言之,攻守平衡的模糊性、美国寻求对潜在军事对手的技术优势的行为,以及中国的努力追赶都使得两国不可能将彼此视为“区域安全伙伴”,也无法参与到应对现有条件下不断涌现的安全忧虑的共同行动中(Kissinger, 2012, pp. 527–530)。
七、难以预料的朝核问题
朝. 核问题集成了上文所述的大多数阻碍因素——战争历史和互疑观念、美国在东亚的防卫态势和同盟体系、与中美大国竞争相结合的朝. 鲜半岛的战略空间。朝. 鲜对核武器的追求是阻碍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Chang & Lee, 2018)。只要分裂的朝. 鲜半岛处于战备状态,一个整体的同盟军事体系就仍有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反过来又使得对立阵营的原有观念难以改变,因此中美的安全困境几乎不可能缓解。从中国和朝. 鲜的近邻关系、美国和韩国的军事力量部署情况、历史意义和战略价值等方面考虑,朝. 鲜半岛是东北亚的地缘重心(East Asia Foundation, 2016),所以朝. 鲜发展核武器的举动足以被视为新地区秩序建立过程中最难以预测且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朝. 鲜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动因根源于整体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观以及朝. 鲜自身面临的不断恶化的战略环境。除了急需在国内巩固政权合法性以外,朝. 鲜领导人仍有理由怀疑外部行为体对其独立和主权的承诺(Bull, 1977, pp.16–17),特别在维持政权和原有生活方式等方面。上述分析还需考虑一种特定背景,即朝. 鲜如何看待后冷战时代变化的国际环境。当中国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驱动的外交转向冷战后以国家利益导向、务实的策略时,中国已不再能够无条件地保护朝. 鲜的政权安全。苏联的安全保证消失之后,由于中国未在1961年《中. 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承诺提供可靠的核保护伞,给朝. 鲜带来了不确定性。所以,当无力匹敌美韩联军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优势时,朝. 鲜似乎除了追求某种“扳平的手段(the equalizer)”外别无选择(Baylis, 2013, p. 221)。
同时,由于朝. 鲜经济的高度自给自足性,单纯的经济制裁的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考虑制裁之外的更广泛的综合性战略,以及如何化解朝. 鲜的安全忧虑(Farago, 2016; Huish, 2017)。现阶段,虽然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的共同努力已成功地说服朝. 鲜领. 导人回到谈判桌,但中美在上文所述的安全议题上的分歧、中美逐渐升级的贸易摩擦和美国主张的“去核化”步骤都可能构成阻碍。此外,尽管中美表面上都同意在维持制裁压力的同时采取某些缓和措施(Wang, 2017),但双方在对朝. 鲜施加压力的程度及应提供的保证方面存在分歧。美国主要担忧的是其盟国——韩国和日本的安全,以及在未履行安全保障承诺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地区核扩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因地理位置和与朝. 鲜的经济联系而具有更多的斡旋余地,但中国对朝. 鲜的影响经常被夸大(Zha, 2017)。所以,在缺少整体性的、区域性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朝. 核问题仍然会成为区域制度化的障碍。
八、结论和合作的条件
基于从东盟经验中总结出的原则,本文试图解释四种影响东北亚地区形成最低程度的、多伊奇式的安全共同体的潜在因素。其中主导性的障碍是美国在本地区以韩国和日本为锚点所构造的防卫态势,以及大国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地位的战略敌对。从结构和社会—历史视角进行分析,可以提出一些有利于区域走向太平洋共同体的条件。首先,东北亚仍受困于螺旋式上升的恐惧和军备竞赛,缓解此安全困境和超越敌对路径的首要条件是取消现有的对立阵营。第二项条件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相关,涉及有关建构敌对的社会—历史认同的国内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为真正地解决互疑的深层原因,民族主义应被建设性地重塑:三国政府需避免利用外部的“他者”来实现国内目标,而是应推出包含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和思想遗产,以及某种共同事业的叙事,如“同一个东北亚”。最后,我们认为,岛屿争端与国家的社会—历史认同紧密相关,是民族主义得以彰显的依据。所以,第三项条件是东北亚各国可考虑再度搁置岛屿争端,并且建立一个中立的海洋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