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治理】国际关系学科能为逐步发展的全球健康议程作何贡献? | 国政学人第337期
作品简介
【作者】Sara E. Davies,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治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教授。她代表性的个人专著与合著有:Sara E. Davies, Global politics of healt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Sara E. Davies, Adam Kamradt-Scott, and Simon Rushton, Diseas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Global Health Secur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编译】周玫琳(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校对】施榕
【审核】许文婷
【排版】赵怡雯
【文章来源】Sara E. Davies, ‘What contribution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e to the evolving global health agend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6, Issue 5, September 2010, Pages 1167–1190.
期刊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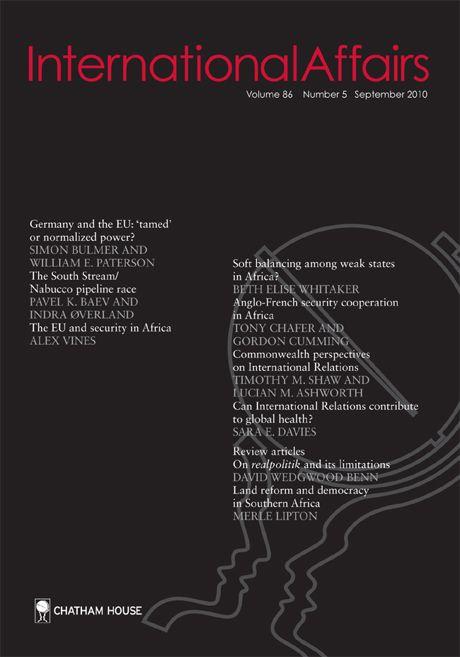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的官方杂志,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创办于1922年。2018年,该期刊影响因子为3.748,在国际关系类期刊中排名世界第5,因其严谨的学术性和政策相关性而备受学术界推崇。
国际关系学科能为逐步发展的全球健康议程作何贡献?
What contribution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e to the evolving global health agenda?

Sara E. Davies
本文介绍了国际关系学科探究健康(或卫生)国际政治的两种主流路径。国家主义路径主要聚焦安全,旨在将健康措施与外交或国防政策联系起来。与之相对,全球主义路径对增进健康的追求不是因为其内在的安全价值,而是因为它增进个人福祉和权利。本文概述这两种路径的发展,并说明为何这两种路径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不断发展的全球健康议程的理解。本文探析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观点如何帮助塑造当代全球健康治理计划,并提出有证据表明两种观点正在融合,这在联合国在健康领域的多项倡议中尤为明显。尚待观察的是,这种融合能否尽可能确保国家利益,从而促进需要全球努力才能改善的个人利益。
编译者注
本文多以“健康”而非“卫生”对译英文中的“health”,包括词组“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健康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health)”和“健康政策(health policy)”等,是为了尽量表意中立,避免“卫生”一词在近现代东亚历史脉络和文化语境中内含的国家主义取向。但实际上,两种译法经常可以互换,望读者理解。
文章导读
本文探究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如何应对健康问题。总体而言,有两种理解健康问题的国际政治的主要路径:一是主要关注安全的国家主义(statist)路径;二是重在聚焦个人福利与权利的全球主义(globalist)路径。本文描述这两种路径,并说明它们如何能帮我们理解如下问题:国际关系学科能为逐步发展的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议程作何贡献?本文概述了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在全球健康议题上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该学科倾向于把健康问题拔高,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塑造为与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同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该学科也意识到,对描述和机制化对健康问题的有效响应而言,“安全”未必是一套有用的语言。
一、“全球健康”议程的出现
在探讨国际关系学科之前,作者首先引介了健康社会学(health sociology)领域的研究成果。关于健康的研究与实践原本聚焦在微观层面,关注医学专业如何应对个人疾病、保障生理与心理的健康。这种聚焦排除了社会环境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而健康社会学家们强调,个人健康是被更宽广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理解塑造健康的经济、文化、政治与科学环境,才能了解健康的意义与实现方法。
在国际领域,与健康问题相关的角色与环境也大幅拓展。国家健康政策条款的形成与有关国家间关系和国家与其他行为体关系的国际考量密不可分。与此同时,更丰富的国际社会规范和政治经济考量都影响着人们对如何追求健康的期待。包括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医药公司、私人捐助者和国际组织等在内的行为体推动了各种健康议程,影响着各国国内健康资源的优先排序。国家、国际社会和包括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组织在内的其他行为体,都具有影响健康机会和结果的权力。
因此,在研究健康问题时,不应只对国家行为体给予关注,而应承认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从全球视角出发提供了一种理解这组关系的方法,这意味着对如下状况的认识: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决定我们健康的行为体与因素并不只是被个人、医生、国家、国际领域之间的线性关系所影响的,而是被一系列在不同处境下采各种互动的复杂因素所塑造的。由此观之,认识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会影响健康成果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力量会导致个人、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相似的现象采取截然不同的反应。
世界政治是塑造医疗保健享用权、医疗保健质量和病愈可能性的综合环境。更重要的是,如今全球因素在保障地方健康上和地方与国家因素同样重要,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来思考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这要求我们对全球、国际、国家和地方影响健康的力量有更好的认识,并探究如何驾驭这些力量才能对全球健康问题作出积极贡献。
二、联结国际关系学科与健康
从形成伊始,国际关系学科就主要研究国家(states)与战争预防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理想主义者(idealists)”就开始追求制止战争,促进国家间和平。国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焦点,但国际“体系”或“社会”的其他行为体(包括个人、公民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也由于它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显著影响被日益纳入讨论。于是,对安全与和平(或秩序)的追求要求拓宽国际关系学科的本体论。自冷战结束以来,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出现率先推进了国际关系学科本体论的广度和深度,并开始讨论我们如何理解安全与和平,讨论秩序、权力、身份和利益如何被建构和变化。如今,难民、女性、儿童、教育、环境和发展都在我们世界政治的图景中,毕竟对许多当代自由主义者而言,捍卫公民福利是成功政府的核心指标。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人质疑把国际关系学科的“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开放给公共卫生的“低级政治(low politics)”的价值,也不意味着国家不再是塑造公民健康的主导角色。这种转向的意义其实在于:一幅正确的世界政治图景必须既包含国家对其公民的影响,也包含国家间的互动。
随着过去20年国际关系学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两种理解国际政治与健康间关系的方法浮现出来。本文将其分别命名为“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路径或视角,但它们其实与安全化和批判安全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两者都主要是关于思考(健康问题)和优先化(prioritization)的模式,都迫切承认健康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需要注意,两者都是观点或视角,并非有着各自拥趸的稳定理论,所以同一作者在不同时间可能会表达两种倾向。
如其名所示,国家主义观点聚焦于国家的角色以及健康在国家外交与防务政策中的位置。这种路径主要探究国家如何最好地应对疾病威胁,尤其是通过国际合作减弱这种威胁。典型的国家主义分析运用“安全”的语言,认为健康问题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政治或军事安全时应得到处理。与之相对,全球主义观点和批判安全理论与人的安全理论(human security theory)有更多共同之处,也更倾向于同意把健康概念化为一种人权。全球主义观点从个人健康的需要出发,考虑全球行为体与结构如何影响个人,其分析因素包括贫困、教育、国家行为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产生的健康效应。国家仍是核心行为体,但全球主义视国家为一系列行为体之一,且将个人作为最重要的指涉对象(referent)。相应地,全球主义观点的基本问题是探究是什么令个人不安全或不健康。国家主义观点倾向于优先保障国家安全,将其视作良好健康的前提;全球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不应自动获得这种优先级,因为有许多有潜力的治理体系可能更好地保障个人健康,国家只有在切实改进人民健康时才被重视。这两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
国家主义(STATIST) |
全球主义(GLOBALIST) |
|
|
指涉对象(REFERENT) |
国家 |
个人 |
|
行为体 (ACTORS) |
国家 协助或减弱国家响应(健康威胁)能力的行为体
|
个人 国家 捐助国 邻国 国际组织 私人捐助者 跨国公司 公民社会组织 |
|
威胁 (THREAT) |
某一特定疾病是否会威胁国家? |
面对疾病,谁是最脆弱的? |
|
响应 (RESPONSE) |
加强保护国家体系的制度 |
若干最可能减弱疾病对个人影响的行为体与制度 |
|
精神主旨 (ETHOS) |
由国家来管理健康威胁是最合适的 |
由任何能减轻威胁的行为体/制度来管理健康威胁是最合适的 |
下文将对两种观点分别详述并评估,说明它们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学科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贡献。
三、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视角
国家主义视角
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传染病爆发会对国家健康及经济政治稳定性带来威胁,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聚焦传染病威胁,许多西方政府也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发展响应机制。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是被地方与国家组织管理的,例如地方理事会保证洁净用水,国家政府提供疫苗接种项目、确保感染人群的隔离。公共卫生曾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当健康政策在国际层面上受到罕见的讨论,通常是因为它与鼠疫和霍乱等传染病爆发有关,或是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领导的消灭天花的大规模免疫项目有关。在传染病爆发过程中,关注重心被完全放在疾病起源国的责任上,而国际努力重在通过信息告知和检疫隔离措施的结合以及海空交通的规制,发展防止该疾病传播到国界之外的机制。有学者批评发达国家在抵御传染病上过于自负。从很多方面看,由WHO牵头的灭绝天花项目只是加强了这种自负。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艾滋病病毒(HIV)的出现以及对其威胁国家团结与经济的认知,健康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的视域。
作为回应,一批学者呼吁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学多关注艾滋病蔓延带来的经济、人道、政治与安全后果。费德勒(David Fidler)和普莱斯史密斯(Andrew Price-Smith)呼吁国际关系学科评估传染病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利用对传染病与国家能力间关系的量化分析,普莱斯史密斯认为“传染病构成一种可证实的对国家安全与权力的威胁”。援引“健康安全”这一术语,他提出警示:传染病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造成严重问题;健康安全即指一种由于病原体消灭核心人口基数而对一国经济与政治稳定性造成的威胁。与此思路相似,费德勒坚持认为,伴随着21世纪抗药性微生物所增加的风险,“理解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政治,或‘微生物缘政治(microbialpolitik)”变得十分重要。这种“微生物缘政治”是两种影响的产物:一是传染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二是国际关系结构与动态对传染病及其控制的影响。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新型传染病与抗药性传染病的双重风险需要政府将其视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加以解决。
与之相似,佳瑞特(Laurie Garrett)也认为公共卫生体系和政治或社会稳定性互相影响:“蔓延的政治失序或反政府主义可能会削弱公共卫生体系,而一场公民健康危机也可能拖垮一个政府”。这些思想渗透进健康的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被WHO所接受。例如,该组织2007年的报告中发展了强调健康与安全之间联系的国家主义观点。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接受这一观点,例如奥斯特嘉德(Robert Ostergard)所编的题为《艾滋病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著作也包含这一主题。
总体而言,国家主义论述的根本观点是:如果健康问题被呈现为类似于核扩散的国家安全威胁,即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国家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WHO和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对其更加重视。问题是,通过强调安全化来解决健康危机,可能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最致命的疾病及其原因转移到那些具有“头条”性质的问题。安全化需要关于外在威胁来源的共识,并涉及一套关于识别威胁来源和指涉对象的特定逻辑。这种特点使其很适合解决紧急危机,但不太适合解决慢性健康危机。例如,把生物武器和大流行性流感视作安全威胁,能够促进针对这类特定健康危机的预防政策,但不能减轻传染病的潜在成因,如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落后的医疗保健,还可能把资源从这些领域撤走。虽然这些因素经常导致病原体的传播和抗药性的产生,但不易被安全化。影响大量世界人口的健康问题也并非都是传染病的结果。
围绕国家主义视角,本文又指出其他三个要点。第一,通过使用“安全”这一传统语言,国家主义者将一组“内与外”的动态关系引入了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关系。如沃克尔(Rob Walker)所论,安全在传统上总与敌友结构联系在一起:要捍卫“内”,抵御“外”。在健康问题的国际关系上,国家主义者仍然视国家为主要指涉对象与主要行为体。国家的角色是保卫自身及其公民免受来自外界的威胁。尽管国家主义观点呼吁一种提高健康问题优先级的新安全话语,它还是依赖于对“威胁”的传统认知。因此,这种观点把艾滋病和流感等健康问题视作必须被击败或扼制的外敌威胁。这明显是一种过度简化,但人们(由此)有一种大概的认知,即安全化是提高健康在国际关系中政策优先级的有用策略。
第二,国家主义视角把关注点压倒性地放在传染病上,尤其是艾滋病、耐药及耐多药结核(MDR TB)、大流行性流感和生物武器病原体。传染病最符合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的安全化理论中对安全问题的定义,因为它在健康问题中最可能构成需要国家进行高强度短期干预的紧急事件。在一些从国家主义观点出发描述健康安全语境中的传染病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中,缺乏控制且普遍的“问题”和危害国家安全核心的“威胁”是重中之重。一些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个别政府的失败,人们才需要集体努力来阻挡势不可挡的微生物的川流。然而,这种对集体行动的诉求很快陷入自我利益的泥淖,因为其逻辑是防止“外”的问题进入国家领土之“内”。依照这种观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修复”他们的健康基础设施,因为这从长期看会保护富裕的、暂时“安全”的西方免受病原体侵扰。国家主义观点对传染病的重视并非偶然,但是,如果把传染病视作一种“武装召唤”的出发点,并期望这会带来全面的医疗保健供给进步,可能注定要失败。因为安全化的假定免除了西方响应任何国界外的健康危机的道德义务。麦克因斯(Colin McInnes)认为,安全化论述把传染病的地位拔高,促使资源被分配到预防传染病在发展中国家爆发上。但费德勒提出,将健康列为对外政策问题有两个难点:一是自满性,即危机会吸引对外政策制定者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但随着危机渡过,注意力也会转移;二是国际健康政策的进步需要政府间协调,这意味着这些进步可能要在优先级上让位于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其他“非健康问题”。截止目前,安全化在调拨新资源从源头上预防疾病威胁上是失败的;相反,应对措施和资源仍主要导向发达国家的自我保护。问题在于,安全化需要实际且迫切的威胁和紧急感,它不适合用来加强对长期预防与能力建设的关注,也不适合用来支持把个人健康作为主要指涉对象 。与国家主义视角一样,健康安全化关注国家层面的威胁,而非将个人健康视作目的自身。
第三,国家主义视角有一个内在矛盾:它一边关注作为威胁体(亦译作威胁代理)和指涉对象的国家,同时坚称传染病是一种靠单一国家无法减轻的跨国界现象。根据国家主义观点,个人健康需要有效的国家结构(来保障)。尽管这种观点认同针对健康危机的多边响应的必要性,其核心假定依然重在保护国家,并使用被认为能激励国家行动的论述。但是,传染病是最常被提及的健康威胁,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两个要点:一是一国所理解的安全威胁(某种特定传染病)未必得到其邻国同样的感知,二是被安全化的健康问题和实际上缩短大多数人寿命的疾病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相关性。安全化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中一个行为体将一个问题安全化,并说服一批受众来接受这一诉求。最严重或最广泛的健康问题未必能成为被安全化的问题。
尽管有上述种种问题,国家主义路径成功地强调了疾病值得政治关注和分析性探究。问题在于,为了让健康问题排上外交和防务部门的议程,国家主义视角采取了一种安全化的方法,这未必适合这一特定领域。本质上,通过将注意力牢牢放在国家上,国家主义路径遗漏了问题的很多其他重要方面,也使部分人的需求优先于其他人。而且,安全化的方法致使关注被放在保护与遏制上,而非解决根本原因,并且把传染病之外的公共卫生问题挤出了讨论空间。导致发展中国家传染病严重的多种条件(贫困、教育匮乏等)也可能在安全化的逻辑中难觅踪迹。这种路径携带如下风险:应对疾病与不良健康状况的根本原因所需要的资源可能被移到另一种用途,即令(主要是富裕的)国家隔绝于传染病的威胁。
全球主义视角
全球主义视角在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政治上有两个基础思想:第一,适宜的指涉对象应该是个人;第二,从国际关系学科视角研究健康问题的目的是促进健康平等。这两种思想都多少植根于批判安全理论,即旨在拓宽和深化安全概念的理论。根据全球主义观点,个人才应是安全的指涉对象,而关注点应放在对个人的威胁而非对国家的威胁上。批判安全理论认为安全问题是社会建构的,安全的意义及其应用涉及到不同声音与议题的优先级排序。
对大多数批判安全研究在健康领域的规范目标的支持者而言,最常援引的术语是“人的安全”,即强调人而非国家才是最合适的安全指涉对象。需要注意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人的安全视作国家安全议程的较小拓宽,二是把安全的主要指涉对象从国家替换为人。全球主义者一般都属于后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了人的安全的基本原则。2001年,绪方贞子(Sadako Ogata)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领衔创立的“人的安全委员会(Human Security Commission)”是该事业的又一座里程碑 。
从健康视角探讨人的安全,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不需要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健康治理,而要重写其规则。在这些文献中,有的分析建议强化既有的地方、国家与全球结构以更好地应对健康问题,更具批判性的研究则考察既有结构如何从源头造成如此严重的健康不平等与不安全,借此证明激进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尽管对既有健康治理结构的批判性研究有显著潜力,近年来这一领域发展不多。这种停滞主要是因为实用考虑:对全球健康体系(包括国家)的激进重塑不太可能迅速发生。相反,变化是渐进的,这促使分析聚焦于相对较小的改革,取得微不足道的进步。相应地,学者们倾向于在既有的主流框架内推进他们的目标,而非创建新的治理模式。他们普遍同意让步的必要性,即进步改革需要从既有的行为体与结构(尤其是国家)获得援助与合作。因此,首要任务是思考如何在不诉诸安全化逻辑的前提下激励既有行为体和结构(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私人捐助者)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行动。
总之,全球主义路径的问题是:是什么使人不安全?应如何应对这些不安全?与国家主义观点相对,全球主义只在国家促进人的安全的条件下重视国家。并非所有“全球主义者”都追求激进地改变既有的政治结构。实际上,他们中有的认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全球行为体可以在国家未能保障人的安全时“介入(step in)”。在这种思路下,许多研究尝试理解全球治理体系如何与国家一同(或在尽管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推进健康项目。在过去数十年中,健康行为体的绝对数量与多样性大幅增加。全球主义路径试图理解全球健康治理中多种行为体的角色,并对全球卫生治理如何产生和运作形成一种批判性的理解,而更激进的会建议重塑治理结构。令(上述)全球主义观点得以统一并区别于国家主义观点的根本观点是:如果只通过国家的视角,健康安全的缺失不能被理解或克服。
当然,并非没有针对全球主义观点的批评。首先,如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论,将安全扩大到包括全人类而不是对国家的特定威胁是不切实际且危险的。例如,他认为安全研究的作用在于协助国家维持秩序,并且预防和准备战争;将安全拓展到传统国家安全之外降低了其连贯性和实用性,且把注意力从使人口脆弱的实际威胁分散开来。如果安全变成了一切,那么同时它也在分析价值上一无是处。其次,人们还有理由批评说全球主义者夸大了国家被其他行为体取代的程度,也低估了国家在响应健康问题时持续的重要性。几乎没有足够的实证成果能表明国家在健康领域的影响力比盖茨基金会或WHO等行为体少。还有人担忧,由于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健康行动的激增,国家提供医疗保健的责任没受到足够重视。
国际关系与全球健康议程何去何从?
尽管有上述各种批评,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观点都正确地指出了全球健康治理显著拓展的事实。如布斯(Kent Buse)等学者所论,国家在健康政策中的角色转变造成公私领域在作用、责任与管辖范围上的模糊;因此,20世纪晚期以来的健康政策议程总面临一组斗争,一边是对解决全球健康挑战的集体努力的需求,另一边是为多样化的(特定)人群和环境制定并传播相关且有效的健康政策的困难。
在世纪之交,联合国下属的不同机构产生的三组文本充分体现了上述看法,它们都试图理解如何在全球主义视角(尤其是“人的安全”路径)上取得更多进步。2004年,“威胁、挑战与变化问题上的联合国秘书长高级专家咨询委员会(UN 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是集体安全的一个新例。该委员会认为健康问题应被视作一种安全威胁,因为它可威胁的对象是无限的,无论贫富。2000年,联合国千禧高峰会(UN Millennium Summit)将180个国家聚在一起,世界领袖们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旗号下同意,截至2015年,全民健康应在流行性传染病、降低儿童死亡率、提供安全饮用水和足够事物以预防疾病、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这些具体方面得以实现。1999年,联合国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for the UN)成立,旨在决定如何实现健康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其2001年发布的成果强调,贫困国家的沉重疾病负担对全球财富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成百上千万的贫困人口之所以因可预防和可治疗的传染病死去,是因为他们缺乏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卫生设施。千年发展目标从此被视作优先考虑世界穷人健康的一项尝试。
上述机构及其文件,都体现出一种放弃传统主权观念及“内/外”之别的尝试。它们都尝试建立围绕健康的集体责任,并认为健康威胁并非被国界所定义,而是被威胁个人的贫困、环境破坏和可预防传染病等要素定义的。国家主义路径成功唤起了对更宽广的安全概念的全球意识,而全球主义路径则成功推动了对安全“自下而上”的思考。
部分由于国家主义视角在收获世界关注上的成功,一些偏向于全球主义视角的学者或机构开始用国家主义者的术语来包装他们的论述。例如,上述有关健康安全的联合国报告都通过国家主义论述来指涉那些如果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问题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威胁。本质上,这些报告中的立场和国家主义路径并非没有相似之处:为了激励行动,我们亟需发达国家意识到贫困世界中因传染病而死的人的威胁也是对他们的威胁。
这种矛盾在“共享世界,共享健康(One World, One Health)”战略框架中也十分显著。该框架是在2008年10月召开的国际禽流感及大流行流感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其首要目标是通过协调全球努力来控制H5N1病毒、防止人类流感,加强疾病监测投资,保障基础服务与系统的延续性,减轻大流行性传染病对社会、治理体系、公共卫生与全球经济的伤害。这一框架中有清晰的全球主义观点,但很明显,其全球主义愿景依赖于国家的承诺,全球治理框架在多大程度上能越过国家政府直接向个人提供健康是不明确的。与这一战略同时启动的是联合国内的全球健康与对外政策议程,该议程是受2007年的“奥斯陆部长级宣言”的启发形成的。该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在三个主题上投入更多努力:“全球健康安全的能力建设”、“面对全球健康安全威胁”和“令全球化造福所有人”。该宣言没有体现关于“全球健康安全”意涵的共识,但它的倡议说明把公共卫生联系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未必是消极的。2008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开始推进该宣言提倡的议程,这促成了2009年第一个关于全球健康与对外政策的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诞生。该决议建议联合国秘书长与WHO总干事协同分析对外政策与全球健康相关的挑战与行动。联合国秘书长随后发布的声明也没有呼吁新的机制,而是强调对既有结构的利用。
在上述一系列行动中,主权国家依然是责任的来源。所有的倡议都是关于国家如何创造并支持有利于全球健康进步的政治环境,并督促国家制定能响应公共卫生与健康安全问题的对外政策。问题依然存在:即使引入新行为体能增加解决健康问题的可能性,进步的观点仍要在既有的结构中推进。此外有证据表明,在未给新行为体赋权的情况下令其在既有结构中增加互动,反而可能更让富裕者通过剥削贫穷者满足其健康与经济利益。简单地增加行为体与行动未必能推动医疗保健进步。这一领域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四、结论
本文描述了关于健康与国际政治的两种主要视角。国家主义视角运用安全的语言来强调健康是应被纳入外交与防务政策的问题;弱政府在保护公民健康上表现不佳,而稳定的治理保障良好的健康。运用安全化(的理论和策略),国家主义视角旨在把健康问题提升到“高级政治”领域。因此,国家主义叙事经常把健康问题(如传染病)等同于国家安全威胁。于是,为了唤起有关威胁构成的传统安全认识,这种视角关注一些特定的健康问题(如艾滋病或大流行性流感)。结果,那些不能轻易引用“威胁语言”、不能唤起足够恐惧或关切的健康问题在国家主义视角中是缺席的。
与之相对,全球主义视角关注个人健康需求以及国家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全球主义视角不预设国家必然是为个人提供健康的最重要或最合法的行为体,它倾向于承认多样的健康问题,因为它主要关注影响最多人而非国家安全的健康问题。这种视角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它会导致国家的重要性被轻视,另一方面其宽泛程度带来了分析上的不清晰。这导致一些全球主义者使用国家主义者推崇的安全化语言来呼吁更多资源投入人的健康。这种援用策略自然也有如上所述的安全化的问题。
尽管有这些问题,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路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合流,框定了我们如何思考关于健康(领域)的国际关系。例如,两种视角都把传染病视作安全问题,尽管国家主义者把特定的疾病安全化以保护特定的民众,而全球主义者把传染病本身视作问题,无论其威胁的人身在何处。实际上,如果不利用传统的国家主义关切,不把健康问题描述为国家稳定的潜在威胁,(研究与治理)进展寥寥。尽管这种路径是一种实用(甚至唯一现实)的政治策略,我们需要认识到其中的危险。至少,这有可能把优先权从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解决根本问题转移到对特定传染病的扼制。因不洁饮水而死的儿童、因无法负担抗生素费用而死于肺部感染的成年人、因不安全的流产而死的妇女……他们都不能唤起令国家选择变革规则的威胁意识。一方面,人们倾向于把健康问题拔高为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在关于健康问题的有效应对的描述与机制化上,安全未必是一套有用的语言。这就是目前医疗保健事业与国际关系学科、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共同面对的困境。



